01.贵客啊,毋让那旧情蒙尘。
我从没想到这样一个清新宁静的山谷里会坐落着这样一个气派的山庄。如果不是因为骤雨催促,我满可以欣赏一下与山谷风景相得益彰的花园,还有围墙上精美的金色提灯,而不是一身狼狈地匆匆敲开别墅的门。
粉色头发的女孩一脸惊讶,这让我反倒更加窘迫了。
“你是……?”
“抱歉”,我尽可能不失礼貌地往里站,以免风吹来的雨丝打湿我的后背,“我是去树庭求学的学生,呃……白厄阁下写了介绍信来的……”
“让她进来吧,风堇。”屋内传来了一个温和的女人声音。
被称作风堇的女孩忙把我迎进来,给我披上一层毯子:“真是不好意思,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给你沏壶热茶来。”
我小心地在沙发边缘坐好,抬头便看到了一张精致美丽的脸庞。她优雅地坐着,披着一条月白色的披帛,即使是居家型的穿搭也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只消一眼,就能看出她绝非一般家庭出身。“我是阿格莱雅,这些日子就请你暂住寒舍,贵客。”她冲我笑笑,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热起来。
风堇很快端来热茶,低声向阿格莱雅说了些什么,便匆匆告辞。
“她是我们这片教区的医生,也是你的学姐。”
我贸然造访时已经是下午。缇里西庇俄丝女士——据说是阿格莱雅年轻时的家庭教师带我熟悉了一下山庄的环境,家仆衣匠为我打扫出一间客房。晚餐很简单,燕麦粥,面包和沙拉。用完晚饭后,阿格莱雅靠在软枕上织毛衣,缇里西庇俄丝在沙发另一端翻着一本厚厚的书,我则坐在壁炉边的地毯上竭力算着繁杂的炼金术式。炉火暖洋洋的,不一会儿我就开始走神。客厅收拾得井井有条,大部分饰物诸如沙发地毯,都用了暖白和浅黄色,大方却不奢华。壁炉上方挂着一幅似乎是关于泰坦神话的油画,正对着铺了米色桌布的长餐桌。一旁用于休闲的角落里,摆着一架古典钢琴。琴身锃亮,另一把乐器——看上去品质上佳的小提琴,却好像久久不曾用过。除此之外,这座山庄,再无他人生活的痕迹。
我盯着正清洗厨具的衣匠看,她面无表情,并不解答我的疑问。
我躺在柔软的床上,疲惫很快席卷了全身。在意识模糊前,我听到了女主人和她的老师的私语:
“看起来雨要变大了,阿雅,小飞儿她······”
“······吾师。命衣匠为她留几盏灯吧。”
伴着渐急的雨声,我想起阿格莱雅那双青色的眼眸,它们······似乎无法聚焦?
第二天,我一睁眼,就看到衣匠垂手立在床边。
我吓了一跳,拖着混沌的大脑和即将再度合上的眼皮从床上爬起。“客人不必惊慌,我只是奉女主人之命送上新衣,还请客人稍作整理。主人及老师会亲自将您引荐去树庭。”说着,衣匠将一件制式新颖得体的衣装送上,又关好房门,留下隐私空间。
我换好衣服,拉开房门,衣匠在门外等我。
“这衣服像是手工制成,可为什么如此合身?”
衣匠波澜不惊的脸上闪过一瞬的自豪,“阿格莱雅女士曾是奥赫玛城内首屈一指的制衣师,凭目测确定您的尺寸易如反掌。”
我只能说是相当惊愕,踏上马车时阿格莱雅认真打量了我许久,最终满意地点点头。缇里西庇俄丝女士留下照管庄园,她与衣匠陪我驱车前往树庭,一路上雨后的风景美不胜收,阿格莱雅却目不斜视,搞得我每每侧目都相当不自在。她大约看出我的疑虑,开口道:“不必在意我,贵客。此处胜景的确宜人,只是我见过太多次,故而不太感兴趣罢了。”“怒我冒昧,女士,”她这份出人意料的体贴让我忍不住接话,“您的眼睛……”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她倒是很不以为意,简洁地解释:“家族遗传的眼疾,有时难以视物,但自理生活还是无碍的。”我点点头,没再追问下去。
马车停在了树庭门口,一只脚刚踏上地面,一个白发的高个青年就飞也似的扑了上来。
“白厄!稳重点,这可不是学者该有的作风。”一个冷冰冷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白厄冲我眨了眨眼,无奈地退到一边。这时我才看清那声音的来源,一个青发的学者,右侧留一绺长辫,左眼似乎受过伤,用眼罩蒙着。他身后跟着风堇和一个淡紫色长发的姑娘。阿格莱雅此时也下了马车,学者的脸色更难看了。白厄把我拉到一旁,小声道:“这是阿那克萨戈拉斯老师,他说话一直这样,你以后就知道了。”
“阿什么老师?”
“哎没事,我们都叫他那刻夏老师。”
风堇和那个叫遐蝶的女孩也站了过来。那刻夏和阿格莱雅……我敢保证他们绝对关系匪浅。那箭拔弩张的气氛,绝不该是陌生人之间所有。
“呵,金织女士竟然大驾光临,怎么,这是你的亲眷,还是眼线?”金织,是阿格莱雅在奥赫玛时的名号,从那刻夏口中说出却满是嘲讽,“只是应白厄之托替求学之人引见一位老师,因主观思怨便恶语相向,同样不是学者的作风,阿那克萨戈拉斯。”阿格莱雅不惊也不恼,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那刻夏往我们的方向一瞟:“白厄,你可真给你的老师省心。也罢,就让我看看,这个由一位毫无人性还仅自昏盲的女士引荐的学生,究竟成色如何。”我和白厄同时打了个寒战。
“有劳了。”阿格莱雅淡淡地客套一句,复又转向我:“我还有要务在身,衣匠会承担起接送你的职责。”说罢,她踏上马车离开了。
那刻夏的脸色还是很难看。“那刻夏老师……”我试探性地开口。“第一,别叫我那刻夏——”他尖刻地打断我,“你也看到了,树庭不提供住宿环境。所以,不许迟到早退,更别带着那女人来见我。”“不提供住宿,那您……”我忍不住问道。
“第二,沉默是金。”他哼了一声,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对视一眼,亦步亦趋地跟上。
这是我求学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两个人如呼吸一样自然的对峙。好在白厄、风堇和遐蝶相当友好,才慢慢抚平我的顾虑。我能感觉到,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就要浮出水面了。
02.往昔啊,显现那前尘旧梦。
我很快就习惯了树庭的学习生活,被阿那克萨戈拉斯老师——其实我们平常依旧喊他那刻夏——突然点名、被他刁钻的问题难倒,然后接受他尖锐的批评——也都成了常事。只不过,在树庭和在山庄如同身处两个世界,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在其中一位面前提到另一位的名字,仿佛那刻夏和阿格莱雅这两个名字从未产生过交集。
遐蝶与白厄住在镇里的修道院,风堇则以教区的医职人员的身份定居教堂。偶尔,衣匠会奉主人之命请他们来山庄作客,我们便更加熟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受过阿格莱雅资助的孩子——包括被她收养,如今却不知所踪的赛飞儿。
一日阿格莱雅携衣匠出门,我们几个便围坐在壁炉边闲谈。
“阿格莱雅女士和那刻夏老师为什么总是针锋相对?”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白厄使劲挠了挠头:“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刻夏老师欠了阿格莱雅女士的钱,然后······”他编不下去了。
“你要是把这敏捷的思维用在论文上,就不会被教授骂那么多次了!如果迈德漠斯阁下在,他就会这么说。”风堇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
“我觉得不像仇人;”遐蝶小声说,“不然老师根本不会教我们这么久。”
缇里西庇俄丝笑着端来茶点,并未责怪我们背后议论的失礼,“原来你们都这么想知道呀,我可以透露一点点”,“她坐下来,”别告诉阿雅哦。”
她像一个博学的老师,带我们拼凑出过往的全貌。
那刻夏出身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约莫十岁左右,一场瘟疫席卷了村子,只有被姐姐送去镇里学习的他幸免于难。没人知道他从前是什么样子,仿佛他生来就如此孤僻乖张,失去亲人的他孤身流浪镇中,被时任教区统帅的刻律德菈捡到,统帅惊讶于他天才般的炼金头脑,不顾他张牙舞爪的反抗,将他带回奥赫玛的中央教廷。在那里,他遇到了阿格莱雅。
阿格莱雅是墨涅塔祭司家族的小姐,穿着光鲜的她第一次见到灰头土脸的青发男孩,一路小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来转去,捂嘴偷笑:“你瞧,这多不得体呀!”缇里西庇俄丝敲了下她的脑袋:“阿雅!怎么能这么说话!”阿格莱雅撇撇嘴,躲到了刻律德菈身后。
那刻夏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个比自己还矮一截的小女孩,“浪漫”真是最没用的神明,他想。刻律德菈将他纳入“理性”的阵营,命他钻研炼金术和逻辑学。他不满刻律德菈为巩固教权摆弄他人命运的做法,更不满如今只能寄人篱下的处境。他把自己埋进被他人称作“渎神”的研究之中,甚至有时会通过签文和神谕和瑟希斯吵上大半天。
他总能在大厅里遇到那个金色的身影。她又娇气又任性,总是小跑着,凑到他跟前问个不停,甚至自顾自地量他身体的尺寸,做好新衣给他送来。他总是以刻薄的话语,或仅以沉默回应她好像永不熄灭的热情。
一日他们坐在光亮的大理石台阶上,她问:“你以后想做什么?”似乎她清楚他不会回答,于是自顾自地接下去说:“我会成为最优秀的祭司,而且我的织物一定会成为奥赫玛的时尚风向标!”阿格莱雅好像是孤独的,从小长在大户人家,接受最严苛的教育,只有她的老师与她为伴。或许正因为此,她才会对那刻夏喋喋不休。
他看着她因为谈到理想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心中突然生起些恶劣的想法。“你真傻,这些泰坦都是假的,祭司见不到泰坦,你也当不了祭司。”他轻蔑地说。“你骗人。”她头也不抬,卷弄着一缕金发。
“不信?呵,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神话证伪。你信它们,不如信我。看看你引以为傲的浪漫,帮得了你什么。”
她“噌”一下站起来,满面通红:“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那刻夏看到她清澈的眼睛里蓄满了眼泪,“我要、我要告诉老师!”她跑了出去,那刻夏看不到她的眼泪有没有流出来。
他把阿格莱雅气坏了。他不认为自己说错了,自然也不会去道歉。只不过,他承认,看到她眼泪的那一刻,除了如同实验成功的得意,他的心不由自主地狠狠跳了一下。
后来,阿格莱雅再也没有找过那刻夏。
那刻夏当然不会在乎他身边有没有人,少了还是多了谁。只是他再从大厅路过时,总看到阿格莱雅一个人坐着,仿佛融入了身后的泰坦造像。
“呵,养尊处优的娇蛮小姐,连个伙伴都没有,足可见其为人了。”他终于忍不住高声嘲讽道。
阿格莱雅把头一扭,一句话都不说。
良久,她才闷闷地开口:“你又何必找我这愚钝的信徒讲话?还是说,这不过是你的表演,而我恰好是唯一的观众?”“你想多了,”那刻夏斩钉截铁地回答,“刻律德拉让我通知你,解语爵和斯缇科西亚将军之子的联姻已经定下,不日将举办婚礼。”说完他转身就走,直到走近门口,他才停下,背对着她道:“因为几句实话就放弃自己的理想?你还真是娇气。”阿格莱雅终于笑了,她跳下台阶,追上了那刻夏的脚步。
婚礼这样热闹的场合,阿格莱雅决不会错过。时光荏苒,她出落得更加漂亮。也不会再像幼时那样,为了摘取一片金色的叶子,在树庭嬉闹不已。那刻夏眉眼的棱角更加分明,神情依旧冷峻,却还和阿格莱雅保持着联系。前些日子他没日没夜地研究新课题,众人再见到他时,他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还有——一只再也无法摘下的眼罩。
“你这是怎么了!”阿格莱雅捂住嘴,险些惊叫出声。
那刻夏对她的反应嗤之以鼻:“炼金术的原则,等价交换。”
“还挺神秘,”她伸手去碰,“痛吗?”
“不痛。”他侧身躲过。
婚礼那天,阿格莱雅精心打扮,盛装出席,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政治联姻远比她想象得无聊。文绉绉的官腔和装模作样的客套弄得她脑袋发晕,一阵应酬结束后,缇里西庇俄丝一转头,顽皮的少女就不见踪影。
另一边的那刻夏不胜厌烦地从学术恭维和愚蠢问题中脱身,穿过舞池,绕到后花园。不出他所料,阿格莱雅果然在这里。她坐在秋千上,身披月光,四周只有虫鸣和风吹叶动的声音。“阿那刻萨戈拉斯?”她跳下来,迎向沿着小路走来的那刻夏。“是我。”他应道。他们并排走着,走到秋千旁。“怎么偷跑出来了?大家闺秀就这种做派?”那刻夏讥讽道。阿格莱雅眨眨眼:“没有浪漫的仪式,也没有金丝相系的真情,真是无聊。”
她又开始荡秋千,他在旁边站着。
“你说,这是爱吗?”阿格莱雅仰起头,看他。
“我不知道。”这倒是实话,而非刻意的敷衍。
“那么,什么是爱?”
这一次他以沉默作答。
“没有爱的姻缘,到底算是什么?”阿格莱雅显出苦恼的样子,
“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阿格莱雅,”他轻声说,“联姻、施舍、恩惠泯灭人性,利用一切……都只是私欲。”那刻夏第一次凝视她的眼睛:“但愿你不会变成这种人。”
她定定地望着他,直到他硬生生别开视线。“算了,”她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让我看看你的成果吧,是什么要你的一只眼睛作代价?”
那刻夏犹疑了一瞬,拿出一个炼金口袋。里面装着一个透明容器,一团明亮的火焰在其中跳动。“灵魂之火,”他道,“具体成分仍在解析,似乎能联通所谓的冥界,但稳定性不佳。”阿格莱雅眼中满是惊奇,同时她看到了那刻夏的眼睛——像海面上燃烧的火。“它不会熄灭么?”她问。
“也许会,”他缓缓地,但语气坚定地说,“但我会让它复燃。”
“回去吧,”他伸出手,“可否赏光与我共舞?”
03.歧路啊,可知那断情难续
无知而天真的少女初次面对真正的苦痛,是墨涅塔大祭司的离世。
葬礼之后,那刻夏经过阿格莱雅的房门,他听到许多声音,唯独没有阿格莱雅的哭声。“她大小姐脾气又容易心软,恐怕——”“海瑟音,我又何尝不知?但眼下别无他法,她也并非不知轻重。”“阿雅,别怕,我们陪着你,就像从前那样,好吗?”
………
面对师长亲友的劝慰和关怀,阿格莱雅抬起头,站起来,开口时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吾师,无需多虑。我已决心承担应负之责,绝不逃避。”
那刻夏没再听下去。他闭了闭眼,离开了。
那次舞会后,他们成了旁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甚至有人将他们与瑟希斯和墨涅塔脍炙人口的爱情神话相比,尽管那刻夏和阿格莱雅的相处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二人谁都没有打破那其实已近乎不存在的芥蒂,或者说,窗户纸。
在那刻夏眼里,阿格莱雅对“统治者”的位置适应得相当快。稚嫩、天真这些少女应有的特质仿佛一夜之间从她身上消失,只有那份坚韧善良不曾有损——他原本是这么认为的。阿格莱雅成为新任大祭司后,眨眼间便被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不得不久居奥赫玛掌握局面。那刻夏对此颇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前往阿格莱雅的私宅定居,在树庭继续深造。
所谓私宅,就是如今的山庄。
他们曾在这里共同居住过一段时间。闲时阿格莱雅喜爱制衣和弹奏钢琴,而颇有音乐天赋的那刻夏,时常与她合奏。“哼,你以为我会同你一起,做这些无聊且无意义的事么?”看到阿格莱雅捧着一架小提琴踏进家门时,那刻夏冷笑一声。阿格莱雅清楚他的性子,并不强求,自己上楼去更衣沐浴。当她边擦头发边走下楼梯时,看着木着一张脸调琴的那刻夏,不由得绽开一个微笑。
“收起你那小人得志的表情,阿格莱雅。”他不自在地别过脸,“也别把我当成一个学术白痴。”
阿格莱雅不置可否,含笑的眼睛看着他,等待他的表演。一曲终了,她鼓起掌来,那刻夏却始终没有将视线从她脸上移开。
她……是不是很久没这样笑过了?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阿格莱雅甚至不再回山庄居住,二人仅凭书信来往。或许理性天生就缺乏浪漫感官,那刻夏只知道阿格莱雅的文字愈发清冷疏离,来信越来越少——直至彻底断了联系,却没意识到这代表了什么。
阿格莱雅的政治手腕为她赢得了一席之地,令她成为代表皇权的元老院口中深恶痛绝的“妖女”。几年后再度相见,是那刻夏收到了阿格莱雅以官方口吻写下的邀约。
她高坐在大厅之上,神情淡漠。“神悟树庭的阿那克萨戈拉斯,”她开口,声音里只有公事公办的冷峻,“烦请你忍痛割爱,交出灵魂之火,并留在奥赫玛履行神使的职责。”
那刻夏扯出一个嘲讽的笑。他不是不知道,那群卑鄙的元老无所不用其极,用毒素暗中毁掉了她的眼睛,经年累月的工于心计消磨掉了她的感情。她谋篇布局,铲除异己,连树庭如今也有她的势力。这不是他认识的阿格莱雅,或者说——这就是“阿格莱雅”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若是拒绝呢?”他高声问道。
“那么,我可能会动用特殊手段。”她一抬手,衣匠立刻握紧手中长剑。
“他们弄瞎了你的眼睛,难不成也弄瞎了你的心?”那刻夏本来心中五味杂陈,话一出口却言不由衷地变成了尖锐的讽刺,“看看你如今的样子吧,冷血、暴戾,是什么让你以为可以随意摆布我的命运?哈,不仅是我,所有人都是你用来达成目的的棋子,是的,所有人,也包括你自己,对么?”
“闲话少叙,我只要你的答复。”阿格莱雅道。
他大笑起来,仿佛这是一场表演,而她是唯一的观众。
“好啊!”他高高举起那个容器,往地上掷去。容器顷刻炸成满地碎片,火焰熄灭,仅留下一捧晶状的灰烬。“既然你想要,拿去吧。”
阿格莱雅一言不发。
“人果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你这簇死灰也不例外,阿格莱雅。”他冷冷地扔下最后一句话,扬长而去。
回去后那刻夏收拾了自己全部的东西,只留下了那把小提琴——他再没踏入过山庄一步,只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研究炼金术,并坚持与阿格莱雅分庭抗礼。元老院得到二人决裂的消息,也曾试图拉拢那刻夏对抗教权势力,却被他狠狠愚弄,势力大削。
阿格莱雅目盲一事传出,她只对外声称是家族遗传所致,并不借此大作文章。那刻夏得知后轻蔑一笑:狂妄傲慢,虚情假意的政治言论。
偶而他会想起那个静谧的夜晚,如今只不过是一场恨海情天的梦。
很久很久以后,阿格莱雅乘车抵达树庭。和她一同来的,还有一个白发的青年。
她将他带至那刻夏跟前,简明扼要地说明来意:“哀丽密谢的白厄,是个可塑之材,希望能跟着你学习。”那刻夏不屑道:“大名鼎鼎的金织女士有求于我?呵,谁知道不是你那为权力实施的手段?”或许是理由不够,或许是有赌气的成分在,他最终收下了白厄。
这个阳光活泼的青年上进且好学,却总搞不懂他这位导师的脾气。
“三天之内交上报告,让我看看你的成色。”
白厄耷拉着脑袋:“新生就是这种待遇么?”
“你是那女人带来的,自然要认真检验,”他抱着胳膊,“你跟着那女人,还不如去找头大地兽。”
“为什么?”白厄挠头。
“敦厚、老实、最重要的——比她通人性。”
他快步离开,只留下一头雾水的白厄。
「金织」的落幕,终于元老院的一场谋杀。
暗杀者们将早已昏聩不堪的她团团围住,短刀闪着寒光,她却毫无惧色。“肮脏的手段,你们就这点本事?”阿格莱雅一笑,迎着刀尖走上前去,鲜血浸透了她的白裙。
大祭司阿格莱雅遇刺,身中七刀,昏迷不醒。同月,元老院罪行被揭露,皇权势力就此垮台。当然,当年留下来的晶状灰烬,实则为记忆残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阿格莱雅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她退居幕后,搬去了山庄休养,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她。
回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看着缇里西庇俄丝,久久没有说话。
“阿雅她,退位之后就把所有财产用作了慈善事业,还有对树庭研究的资助……她自己除了服装店和这座山庄,什么也没留下。”
遐蝶睁大眼睛:“其实,他们之间只是误会吧……”
“或许是,或许不是。他们只是走在了不同的道路上。”我说。
不知怎地,我眼前突然出现了那团跳动的火焰。白厄向我们使了个眼色,于是我们在睡前悄悄聚在了一起。
他一脸正经地开口:“死灰复燃和旧情复燃,你们喜欢哪种说法?”
我们相视一笑,瞬间明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
04.真情啊,毋因那隔阂泯灭
“没用的,”风堇抱着小伊卡,一脸担忧地看着满教室乱走的白厄,“我总是劝老师不要对阿格莱雅女士那样刻薄,但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从没真正改过。”
“老师和阿格莱雅女士的关系……一直如此吗?”遐蝶轻声道,“从那天的回忆看,他……还是放不下阿格莱雅女士的吧。”
“他是个被墨涅塔诅咒的人,”白厄抱住头。
万敌往椅背上一靠:“这话还是送给你最合适。”
我感觉赶工实验报告都没这么费脑筋。正当愁眉苦脸的我们相对无言时,冷不丁冒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呢?研究课题都完成了?怠惰是求学的大忌,还愣在那干什么!还有你,悬锋城的王储,回你的历史系教室去!”那刻夏冷着一张脸站在门口,我们只得灰溜溜地走出教室。
“退一万步讲,就算,就算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我们也希望他们重归于好呀……”风堇揉揉小伊卡的脑袋,向我们低声道。
也许跟着那刻夏也让我们轻视了浪漫的力量。现在想来,我们或许永远都忘不了那个铺满金色阳光的下午。
那天……炼金实验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偏偏这爆炸就炸在那刻夏的个人实验室,他那偏激的性子让他往业已烧毁的坩埚中扔了一把炼金材料,他——我和风堇匆匆赶到时,只看到昏倒在灰烬中的他。
“没什么大碍,”风堇摇了摇头,“就是实验影响加上精神不佳,唉。”那刻夏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听风堇说他一直都在树庭,实验室就是他的起居室。也难怪休息不好。“我们走吧,白厄他们找到了很有趣的东西呢。”她拍拍我。“这次事发突然,牵涉到重要实验资料和材料,下午阿格莱雅女士也会来。”
那刻夏睁开眼睛。已是下午,金黄的阳光落在小小的房间内。他一瞥,那位不速之客仿佛没注意到似的,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翻看着一大叠泛黄的纸张。
他撑起半个身子:“呵,金织女士竟还有看人窘态的癖好。”
阿格莱雅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去看手里的纸:“怒我直言,你还是省省力气,好早点从这里出去,阿那克萨戈拉斯。”“你留在这儿恐怕只会让我病情恶化。”他毫不客气地道。阿格莱雅不置可否:“我离开便是。”说罢,她站起身,留下了那堆那刻下本以为是无趣的政治文书的东西——那是她给他写的信,皆是亲笔所书,被他悉心保存着。
阿格莱雅不假思索地迈出步子的那一秒,那刻夏条件反射般地扣住了她的手腕。
“那些信,是哪来的。”他沙哑着声音。
“你的实验室被爆炸弄的面目全非,白厄他们从你书柜的暗格里发现了它们。”阿格莱雅神情坦然,声音平淡,好像这些信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让那刻夏心里不禁有些恼火,却无法言明,只得拧着眉毛,把脸转向窗外。
“那时的我竟还能写出这般文字。”她话语中颇有些感慨。
那刻夏冷笑一声:“如今你却是这幅模样。”
房间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
良久,那刻夏似乎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他开口道:“既然都到了这步田地,那么我也不必再作什么无用的解释了。告诉我,阿格莱雅,那些年,你都亲历了什么。”他并非不知道阿格莱雅遭了多少非人的暗害,但当她真的平静地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讲述这些事的时候,冲击力还是比他想象得大了许多。当她讲到自己已散尽家财重建民主机构和福利设施,他终于出言打断。
“你真是疯了。”
阿格莱雅挑了挑眉:“你也不遑多让。”
那刻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仍旧带着那种傲气,向阿格莱雅伸出了手:
“不妨让我们打破对彼此的芥蒂吧。”
“荣幸之至。”她轻轻将手覆上了他的。
这时那刻夏蹙了蹙眉:“白厄,你不去上课在门口偷听师长的谈话?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个。还是说,你把金织女士那窃听的本事学了个十成十?”
房门轻启,我和白厄活像干坏事被老师抓包——好像确实也是这样,互相推搡着挤进病房。后面是探头探脑的风堇和遐蝶,哦,还有一个抱着胳膊靠在门口,一副自己是被迫的样子的万敌。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阿格莱雅轻柔地问。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
阿格莱雅笑着摇了摇头,站起身来:“我该告辞了,阿那克萨戈拉斯,三日后山庄花园见。还有——你是不是该放开我了?”
那刻夏触电般收回一直抓着阿格莱雅手腕的手:“呵,别自作多情了,我可没说要对你言听计从。”说罢,他把头扭向窗外,一言不发。
我们几人亦步亦趋地跟在阿格莱雅身后,逃也似地离开了病房。
三日后,山庄。
“小夏,好久不见,”缇里西庇俄丝歪了歪头,“阿雅在花园等你。”
“先说好,若无要事,我即刻告辞。”
缇里西庇俄丝笑而不语。
他远远就看到了阿格莱雅。她坐在放在草地上的软垫上,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走向她,还不忘讥讽一句:“约人在自己的私宅见面,却连个就坐的地方也没有,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你可以坐在这里,”她拍拍自己身边的空位,“况且这也曾经是你的私宅,不是么?”
饶是那刻夏这样锋快的口舌也不禁语塞:“你这女人——!”
“我想很多话我们之间都不必多说了,不妨直言,”她假装没看见那刻夏快要崩掉的表情,“阿那克萨戈拉斯,要回来住么?那把小提琴……我还留着。”
“啧,说得好像没有你我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你这女人别太自以为是了。”
“原话奉还。”她淡淡道。
然后是横贯两人之间的冗长的沉默。阿格莱雅不看他,也不急迫,只有风吹动草叶的声音,让那刻夏再度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晚。
“你知道吗?”他兀地开口,连他自己也理不清这没头没脑的话究竟有什么逻辑了,“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但你不一样,阿格莱雅。你是神明。”
“而我恰好是渎神者。”
我的私欲或许是你。他心想。
他笑了,轻蔑地。他将一个透明容器托到阿格莱雅眼前,里面跳动着一团火焰。
“你看,我说过的。”
他看到阿格莱雅的眼睛里也亮起了光,不知是火焰的映射还是别的什么。
“这次的代价是什么?”她问。
“这代价要你来付,阿格莱雅,”不等阿格莱雅开口询问,他就接下去,“你这山庄其中一间房屋的永住权。”
她轻轻一笑:“它本来就是你的。”
那刻夏终于伸出手,把阿格莱雅拉起来。他们一同捧着那团火焰,那里似乎承载着岁月消磨掉的一切情感。
“死灰复燃和旧情复燃,你喜欢哪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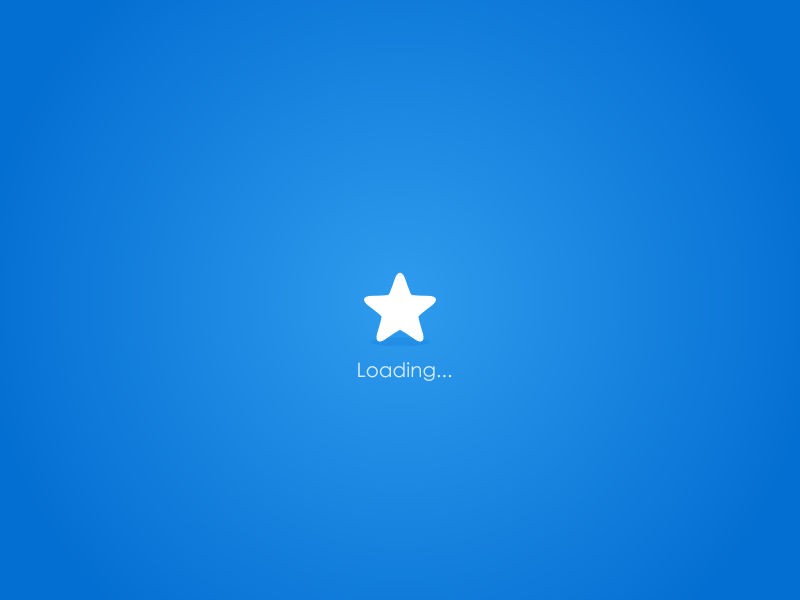
评论(4)